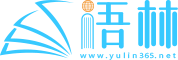世界读书日=买书日+直播日+摘瓜日。
今日所见吐槽。这一天,手机眼睛耳朵都用不过来。无论如何,对于读书人,只要在阅读,每一天都是节日。
所以,我们邀请了杨照、梁文道两位读书人,做客naive咖啡馆播客,回到原点畅聊阅读。
更多内容,请大家关注公号“Naive咖啡馆”
嘉宾 | 杨照 梁文道
主播 | 荣青
本期话题
1. 新冠病毒肆虐全球背景下的阅读和平时有什么不一样?
2. 梁文道谈童年阅读经历,“通过看更多的书或者更不一样的书,来帮助我去具体的体认。”
3. 杨照谈京都历史与京都疫情、闻一多的《秋色》和芝加哥Jackson Park的关系,“阅读真的让我不管走到任何地方,甚至会包括会决定我跟什么样的地方,用什么样方式来看待这个地方”;“我认识这个世界已经完全摆脱不了阅读、阅读决定我怎么跟这个世界发生关系。”
4. 梁文道反问:阅读经验赋予一个地方的“光晕”,会不会也是一种限制?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可能透过读书就能够进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时空?
5. 新冠病毒爆发后,网课、线上办公成为常态,现在还有什么不能线上化?为什么一定要体验或者说这个时代我们还能够讲“什么是体验”,杨照举例《钟楼怪人》,谈巴黎、罗马和毕尔巴鄂的体验。为什么要保有陌生感?
6. 要不要把孔子读成隔壁老王?梁文道谈关于当代人一种实用主义的阅读态度。
7. 是不是每一本书后面都有一个完整的意图和结构?人是不可能故意要盖废墟的。梁文道举例法国古典学者Jean-Pierre Vernant对希腊古典思想的研究,难道人不能够要故意盖废墟吗?
8. 为什么不能把孟子读成隔壁老王?为什么我们不应该一直反复只读同一个时代的书,或者不应该用这种方式去读?我们需要了解人的多样性,现实的情况,或者是现实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太有限了。我们不只关心现实,我们不得不思考未来,我们不得不去想象趋势。
疫情期间的阅读
梁文道:首先我很不习惯,因为平常我一个礼拜起码坐飞机1到2次,最近是我人生中这十几年来唯一一次两个月都飞不了,天天在家里面。其实从读书的角度来讲,分别不是很大,平常无论在路上还是在家还是在哪里,我都会不停地在看书。
现在在家里,我并没有感觉到在家的时间多了,看书的时间也多了,我完全没有这个感觉,反而觉得好像比平常还要忙碌,因为除了看书的时间还有一个问题是,我要用很多时间处理工作的事情,因为现在遥距通讯,其实我觉得花的成本更高,效率更低。但是如果说从读书上来讲,我觉得分别真的没有太大,因为我自己看书并不是太在意环境,在意的是我想看的书是什么书,以及什么方向,有什么计划。
比如说我通常一段时间有一些计划要看什么东西,这段时间大家都很关心眼下的情况,跟传染病或者是全球化方面的东西,因为做节目的需要或者是各种原因,我肯定也会看得多。前阵子我们做节目的时候,恰恰是杨照老师的建议,我做了一些节目,关于经典的和瘟疫相关的文学的介绍,但是抽出来看,其实这些都是本来我平常的状态,本来我就是一个因为做节目、教书或者自己的兴趣,在某段期间我觉得需要读某些书,我就去读。
这段期间,我并没有因为家里面的藏书都在我身边、有很多书买回来还没看都堆在这,所以我就分心了,就觉得我要先看这些先看那些,没有,我还是挺按照计划在看书的一个人。
杨照:在过去的三个月时间当中,我没看任何的电影,所以对我最大的影响反而是看电影。第一个问题是我有这种毛病,老是觉得电影应该要认真的好好的看,不敢在家里随时可以把它停下来、随时去上厕所,所以不到电影院看电影,我的很多电影就不能看,我很想要认真好好看的,就不能看了。
第二个是我很长一段时间电影是在飞机上看的,因为飞机上最适合看电影,包括像这种长途的飞机对我来讲,连看书都非常困难,因为你会很疲倦,这个时候最适合在飞机上看电影。三个月不飞行,我基本上也就不看电影,但是另外一个自己很深刻的反省,我很清楚知道看电影跟看书对我决然的差别。
我必须说像这种时刻我会花很多的时间看书,为什么不去看电影,为什么在飞机上我才会愿意看电影,我老是觉得看电影很多时候是被绑架的。因为读书,每个人不一样,阅读的次数、时间不一样。有一些书,我年轻的时候可能花三个月的时间才能够把它读完,我现在很可能只需要三天,甚至我可以自己决定我读书的速度。但是电影基本上不可能。所以反而在这种状况底下,我越是珍惜我的时间的情况底下我就不看电影。这反而是应该说这段时间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读书没太大的变化,但是电影看的少很多。
4月23号,一般我们就说叫做世界读书日,不过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是我想把世界跟读书这两件事情用不一样的方式把它连接在一起。我觉得我跟文道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那就是我们认识这个世界有相当大的程度是透过阅读,而不完全是经验。
当然文道的经验也很丰富,一个礼拜飞两次,当然你飞了很多的地方,可是我想探讨的或者我想问文道的就是在认识世界、理解世界这件事情,读书、阅读对你来讲到底是什么?你会因为阅读认识到不一样的一个世界,跟世界发生不同的关系吗?你要不要借由世界读书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这上面的一些体会。
阅读与认识、理解世界的关系
梁文道:我们都是因为阅读或者因为读书让自己跟世界的关系和自己对世界的认识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还在台湾念小学的时代,有一个很奇怪的爱好,就是喜欢看字典,但不是为了认识字。在读那些历史的时候,或者上课在学那样的历史的时候,我一直很好奇那些地方,比如说春秋、战国那些国家它到底在哪里?
那个时候因为在小学的年代环境的限制,使得自己读书的视野能够看到东西真的是太少了。所以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做历史地图集。我就去翻一些很大的字典,我记得当年台湾最大部的字典应该是叶公超主编的那一套《国语辞典》,然后我去翻查,另外拿一张中国地图出来用铅笔在上面去画,去想象,根据那些文字的指示,去想象过去的齐国在哪里,楚国到底在哪里,它们的疆域大概长的是什么样子,其实很无聊的事。
我觉得书里面读到的东西好像是少了一点什么,还不够,必须要有一个什么视觉的东西让它更具体的呈现出来。好像文字跟它所指涉的东西之间,好像还有一些联系,不是那么自然而然能够发生的。所以我在想那个指涉到底是什么?忽然有一天下午,好像是周末下午在家没事做,一出门,看到阳光,我忽然有个很强烈的感觉,原来春秋年代的中国人,他们活的世界也是有颜色的,也是有阳光的。
今天照射我头上的这些景物,尽管我在台北,可能秦国的人都也曾看过。那是一个今天看会觉得是很无聊的领悟,但我当时忽然觉得这个世界,书里的世界其实不是黑白的,它是彩色的,我们读历史的时候,古代的人其实跟我活的世界相距并没有好像很远,但是在地球历史上这也只是一瞬间,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而已。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发现读书,像我刚才那么做,当然也是某种读书的练习,比如说我要查地图我要怎么样,但是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读书之后,我发现它给我对世界的重新认识是什么呢?还不只是知道了一些书上的知识或者一些什么观点去认识这个世界,而是一种很具体的感性的东西,是很感官性的。
那个是什么?我在想古代的人感官看到的跟我们今天感官看到的,是真的是完全一样吗?还是说会有一些不一样?于是那个时候开始读书,对我来讲就变得很奇怪了,它一方面好像是让我认识更多知识,更多历史的知识、更多物理学的知识、更多数学的知识、更多化学的知识,但是它总在引诱我去想象,这个世界是否还有其他模样?而当我要好奇的追问那个模样到底是什么模样的时候,我还是必须再去看书,看更多的书或者更不一样的书,来帮助我去具体的体认。
包括后来为什么喜欢读文学、读小说?其实也是因为要知道一种更具体可感的,换了一个人、换了一个空间、换了一个国度,换了一个时间的人,他看到的跟我看到的有什么不一样?我对这种问题非常好奇,然后这样子去看,这样去想之后,我觉得读书看到的事情,它所让我了解的世界,或者我读到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是更丰满的、更多元化的。
那这是我一个小时候印象特别深的一个经历,我不知道杨照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对你来讲,透过阅读认识世界或者阅读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杨照:你刚刚这番话让我想起唐诺,我猜你也有收到这一份“唐诺问卷”,唐诺问卷里面有一个题目让我很困惑,问卷里面有一个问题,说,如果你到荒岛上去只能带一本书,要带哪一本书?这个很痛苦,只能带一本书比不带书还要更痛苦,因为太难选了。我就那样想说,如果真的只能带一本书,我要带什么书?
第一个一定要想说,一定要厚一点,可以读久一点,可以反复的读。我当时本来我的答案是我要带郭庆藩《庄子集释》。我大学时候就开始参与台湾的党外民主运动,那个时候其实情况已经没有那么严峻,可是多多少少还是流传很多故事,写了什么文章,讲了什么话啊,去参加什么会议,就会有警总来找你喝咖啡,然后不小心就被抓进去了。
《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06年版
当时我就觉得我很英勇,英勇是什么呢?我不怕坐牢,我不怕被关,因为我可以看书,只要有书,至少两三年应该没问题。当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郭庆藩《庄子集释》,因为1000多页,看这个书,我一天只需要三页就够了,光这本书就可以撑一年的时间,我就觉得说我已经找到我的答案,可是又想说,如果到荒岛这还遥遥无期,甚至不是有期徒刑,如果是无期徒刑,恐怕连《庄子集释》都不够。
我就好奇说,然后来看一下,唐诺的答案是什么?我一看我就笑了,唐诺比我厉害,他就说他要带《辞海》。你刚问说你的那个年代在台湾,最大的词典,就是《辞源》和《辞海》,我说这个家伙作弊,自己提了一个问题,既然给了这个答案,别人怎么回答呢?他还稍微客气了一点,他没有说《康熙字典》,我说这太好的答案,我找不出更好的答案,我要改变我的答案,我也要带《辞海》去,带《辞海》,我就可以在荒岛上过一辈子,慢慢一个词条看。
这是你刚刚所说的,我自己的阅读跟世界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因为阅读真的让我不管走到任何地方,甚至会决定我用什么样方式来看待这个地方。比如说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我有个特别关注的地方,京都。京都有一部分是当下现实的京都,当我在关注京都疫情的时候,因为读书认识的京都就跑来了。
因为我读书时候非常清楚知道,在当时西元第八世纪为什么从奈良搬到京都来?为什么叫做京都,为什么称之为平安京?日本桓武天皇当时是被瘟疫赶出了奈良,一连串的瘟疫让人心惶惶,再加上政治斗争,所以桓武天皇他要选一个地方,他认为可以平安的离开奈良的各种不同的灾难。
日本桓武天皇。794年(延历13年),就由长冈京,再迁都到了符合五行、阴阳之说,与四神相应之地平安京(即京都,在明治维新迁都东京之前一直是日本的法定首都)
因此京都在选择它的地理位置的时候多么样的特别,这我印象太深刻了,它真的是一个风水大城,这个城它为什么建立在这里,它是一个完全方正的一个城,它有这个东西南北,最重要最关键的就在于它的东北方,东北方是艮鬼,艮鬼是鬼门。当时就是因为有比睿山,接下来有上贺茂、下贺茂。这一路,这一条线,而且你现在去看地理上,真的就是一条线了。真的就是京都的正方位当中的东北。当时在比睿山上有那么一个和尚在那里结庐,到时候甚至不是一个庙,可是这个和尚跟这个山因为这样变得重要了,后来当然就变成了今天的延历寺,就变成了卫护整个平安城的守门,守着鬼门的第一线,鬼门的第二线又有上贺茂神社,再到第三线还有下贺茂神社,这样一整条线连下来保卫着京都城。
所以这个时候去看京都,明明是2020年,但我一直看的是说会不会真的因为这样一个历史的特别选择的理由,让京都可以抗疫。我必须说因为这样的阅读逼得我有点点迷信,看起来京都在整个日本的状态底下,因为风水好,在这次的疫情当中受到的影响远比大阪轻的多,远比东京轻的多。这就是我自己说,我自己感觉到,因为阅读,所以让我跟这个世界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都有着不同的关系。
我自己还有一些非常深刻印象的,比如说芝加哥,一般人可能不会那么在意一个地方叫做Jackson Park。芝加哥很多其他地方我都忘了,Jackson Park不会忘记,因为Jackson Park就让我想到了闻一多,想到闻一多的那一首《秋色》,那首藏诗。然后我永远都会感受到说那样的一个五四的青年,然后到了芝加哥的Jackson Park,感觉到秋天的秋色,写了一首长诗。还不止是这样。我原来也不知道,闻一多写了这诗。
我最早遇到了这个诗又偏偏是在很年轻的时候,还没有出国,当时不觉得自己有机会去到芝加哥,那是在杨牧,当然现在最近刚刚过世,然后他当时还叫做叶珊,叶珊所写的散文集里面有这么样一篇,讲芝加哥,一开头他就讲Jackson Park,然后杨牧坏啊,因为他就在那里,他就说曾经有一个青年在这里写了一首长诗叫《秋色》,他就这样讲,然后那个时代我们读了就把它记下来,但是也没有特别的,因为也不知道这个诗人到底是谁。大概是到了大学时代,然后突然之间在一堆当时台湾的禁书里面遇到闻一多的诗词,看到了这一首诗,心里的悸动说我碰到了,我找到了,原来杨牧讲的是闻一多,原来是闻一多啊。
《他们在岛屿写作》中的杨牧
从此芝加哥对我来讲,就是那个《秋色》,就是Jackson Park,这是我觉得阅读改变了,或者是影响决定了我跟很多地方的关系,我也必须承认说,也许因为这样它有它的坏处,好处是说有些地方它就会让我觉得跟它有非常深切的连接,而不单纯只是一个旅游的地方,或者是甚至在那里居住或者怎么样,它会有一个更深的、多层次的、不同时间的连接;当然也有坏处,我的一些朋友是很清楚,比如说旅行、大山、大水通常对我就变得没有那么多的吸引力,像是北欧的冰峡,或者是高原大山,我通常不太去,因为我去那里我会觉得我跟它没有办法对得上,因为这里没有典故,这里没有其他的人,这里没有当我在读书的时候,我可以先读到,然后因此跟它可以建立的特别的关系。
Jackson Park
这是我自己的一种体会,我必须说,的的确确我认识这个世界已经完全摆脱不了阅读,阅读决定我怎么跟这个世界发生关系,我跟这个世界之间的关系,其实跟我的阅读经验完全就离不开了。
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可能透过读书
就能够进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时空?
梁文道:我的经验跟你很类似,当然我不像你,我还是蛮喜欢去大山大水的。可是我自己觉得阅读真的是会给我们去到的地方或者我们所生活的地方,在脑子里面有一个印记,那个印记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印记,它会左右着我们接触到的眼前的真实的地方,散发出一种很神奇的一种光晕。
但这个东西有时候我觉得也会好像是有帮助,或者是让我们看到更丰富的东西,但是有时候会不会也是一种限制,比如说假设有这么一个人,他可能是个小孩,他没有读过什么书,去了柏林也好,去了伦敦也好,去了你最喜欢的巴黎也好,可能他就看到好漂亮,马路好干净。巴黎的街上有很多狗屎,他就看到这些。但是先读到它的人,还在不断透过书籍重新认识那个地方的人来讲,到了那个地方之后,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我们走过的巴黎街道,我们看到的东西不是此时此刻,比如说如果我今天2020年的4月19日下午,我正在巴黎的话,我走出马路走在街上,我看到的绝对不只是2020年4月19日下午的巴黎,我好像还看到很多重重叠叠的幽灵,整个空间是一个透过魔法才能看到的有一层一层的东西堆叠在里面。比如说走过Saint Germain旁边有一条小巷,你知道那个地方有个咖啡馆,那个地方是伏尔泰去过的地方,是卢梭去过的地方,甚至是美国的本杰明·富兰克林走过的地方。
然后你看到空间历史就完全不一样了,你看到的不只是路边有一坨狗屎,那这是很有趣味的一件事情,反过来它也会制约了我看到的眼前的现实的巴黎。比如说有时候你只注意到狗屎,并不一定是问题,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觉得怎么巴黎那么多狗屎,然后跟着他去问,巴黎这么多狗屎是因为巴黎人喜欢遛狗。巴黎人为什么遛狗?比如说日本,你比较不容易看到狗屎,因为自己主人会清洁,那么他们会认为狗要拉屎是狗的天生的狗权。然后所以为此巴黎每年要花1亿以上的欧罗专门清洁狗屎。当然也许我看了这些书我会注意到,但是我想说的是这种经验有一次对我的影响印象很深。
我年轻的时候,因为我在台湾跟香港长大,一直读到的中国大陆都是书里面的中国大陆。所以当我一旦有机会可以自己一个人背着个背包去大陆的时候,我就很疯狂的背背包到处去跑。有一年我记得我去三峡,我从宜昌开始坐船,就一直到重庆,那么一路上停停坐坐这样子,一路转那些轮船或什么的,当真的穿越过三峡,比如说到了巫峡附近的时候,穿过的时候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我发现我眼前的每一个地方都是我在诗里面读到过的地方,以前的人写过都画过太多,而最有趣的是什么呢?我发现三峡这个地方它沿岸的那些山壁上面居然还刻着古代的人到此一游之后的那些感想的名句。比如说一些很有名的古代的人写的诗句,很有名的游记,一些文章,那些字句,是会被刻在一些石壁上,也就是说像什么?像展开一幅中国式的山水长卷。
《长江图》
我游三峡的时候就感觉到三峡是个写满了字的一个空间,它不是一个天然的大山大水,它是一个被充分人工改造过的一个环境,早在有三峡水库之前。人工改造,就是大家不断在在上面碑刻。比如说我们去泰山也是你看的其实不是一座山,而是沿路的所有人工的这些修筑,所以我当时就有很强的领悟,为什么中国人对自然的看法跟西方人那么不一样,比如说在美国,没有人会在黄石公园刻碑,然后没有美国人会想在Yosemite吟一首诗,然后跟着把那首诗刻在山壁上最显眼的地方,他们绝对不会这么做,他觉得那叫破坏自然。
但中国人自古以来毫不介意这么做。而当这么做了之后,我们就那个看法很有趣,你好像在看到古人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他想到了什么?然后他的到此一游的感想被写下来了,刻在那了。所以你现在看到的这个东西有点像看电影,用一个今天的网络大家比较熟悉的概念,就是你看在手机上,在iPad上面看电影,新一代的人很习惯在手机看,还要开弹幕,那就等于每一个镜头,你同时看的不只是这个镜头,你还在看人家对镜头的评论,这个评论后面还有评论。这个是太中国式的山水了,对我来讲。
所以我就说我当时就会很强烈的感受,就是到底我读到的东西怎么样影响我看到的东西?而我看到的东西里面,在中国这里,它会出现一种很特别的情景是,它还要把以前的人所看到的,李白看过的三峡,它的文字就在我今天看到的三峡的山石上呈现出来。
我印象很深的是你在带领大家去阅读中国原典的时候,你常常强调一个概念,就是距离,一个陌生的概念,我们不要太容易的去把孟子写过的东西当成是他在回答我们今天的问题。其实孟子写的东西是在当年他所处的时空底下写出来的。
他那个时代底下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他认为自己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他的problematic是什么?他去写了那些或者说像庄子这样子,那么你认为我们必须要尽量了解那个时代底下他为什么要提那个问题,而不要轻易的消除掉这中间的时间的界限,要保持这种陌生感。那么所以我一直很好奇,你怎么看这种感觉,这种距离像我刚才举那个例子,当我看到读书会影响我看到一个空间,比如说你去到京都,或者你去到巴黎,你读到的这些书会影响你看到的眼前这个世界,因为你脑子里面是有一些有时间距离的东西在影响你看到的今天。
在中国,我们可能会把以前时间产生出来的东西,也直接留在我今天看到的景象上。但是那些文字所处产生的时代,它所产生的时空脉络跟社会背景,其实离我们今天都非常遥远,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可能透过读书就能够进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时空?我们如果今天读一个以前的人写的书,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可能完全进入到他的状态去理解,然后才能够产生你所说的这种距离感跟差异,或者这种陌生化。
杨照:刚刚讲到说疫情期间,现在大家都不能飞了,基本上连梁文道都不能飞了,就没有人能飞了。谁都飞不了,那又怎么样?我的意思是说会不会我们到时候因为大家都在家里都有互联网可以卧游。我们过去以为当下是real time,以及real space的这种经验都被线上化了,那有什么不能线上化吗?我觉得这个议题会对我们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击,会一直不断地逼我们去想,到底还有什么不能线上化,我必须承认说很多时候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想这个问题我也想到了一些答案,例如说刚才讲到,你为什么一定非得要去巴黎,我们可以看巴黎的照片,多少人去到巴黎,不也就是去埃菲尔铁塔前面,然后去拍个照,我们为什么非得要体验,或者这个时代我们还能够讲,什么是体验?很诚实的说我自己是有答案的。
我的一个答案,举个例子来说,像是巴黎圣母院。当年我们读《钟楼怪人》,然后看《钟楼怪人》的电影,包括现在如果大家去看迪士尼的《钟楼怪人》的电影,它开场的场面,不就是Quasimodo在圣母院的上面往下看,看到广场里面一堆人,我们都看过这些东西,可是我必须真的很诚实的说,等到我真的去到了巴黎圣母院,或者说我去到巴黎,我在巴黎感受到的叫做scale,叫做尺度。
我觉得它最迷人的地方,最了不起的地方,它是一个对的尺度的城市。巴黎圣母院它有多高,它有多大,它外面就有多大的广场。这个广场跟它的建筑物是配合的。它旁边是塞纳河,塞纳河旁边是从Cité(西岱岛)通往市区的桥,所以你从这个桥上你才能够看到圣母院的这些飞扶壁(flying buttress)。你没有这个空间,你就看不到这种美。
巴黎基本上所有的建筑它都是用这种方式安排的。埃菲尔铁塔有这么高,你可以到铁塔底下去感觉到钢铁的重量,但是你一定要记得旁边必然有战神广场,如果没有战神广场的话,埃菲尔铁塔的那种雄壮就没有办法被体会。
相较底下我也是因为走了比如说罗马,让我更清楚地感觉到我喜爱巴黎远胜过罗马。因为同样如果只是借由比如说我们小时候看《罗马之恋》,看到喷泉、看到许愿池,爱罗马跟爱巴黎是一样,但那都是想象。可是去到罗马,我到现在我再也不要去许愿池,那是个痛苦的经验。那么漂亮的一个池子,那么漂亮的雕塑,被塞在空间里面,这不对劲,罗马就是没有这种巴黎必然有的一种尺度的感觉。
《罗马之恋》
或者是说科隆的大教堂,我也觉得不对劲。这么大的一个教堂,广场不见了,广场现在变成了火车站,从火车站一出来,建筑物逼着你,你没有办法像在巴黎圣母院从任何一个角度你都慢慢的靠近它。所以我说另外一个让我也有很深切的非常强烈的印象的是毕尔巴鄂(Bilbao)。毕尔巴鄂,当然最重要的是Frank Gehry。
2009年我去到毕尔巴鄂之前,谁不知道Frank Gehry在那里盖了奇特的建筑物,谁没有看过。去之前看了几百张照片,但是抱歉,你不知道Frank Gehry有多了不起,你非得到那里,不管你是从东边西边进来,沿着河你才能够清清楚楚知道为什么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美术馆选在河湾之处,为什么明明就旁边就是条河,Frank Gehry却要在美术馆的前面还要给它一个喷池,然后用钛金属所造成的光线的作用跟尺度是有关系的,这就非得要体验不可。
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美术馆
所以对我来讲,体验教了我。我们如果想要让自己生命真的过得丰富的话,你就应该用这种方式去体验,要不然的话你可能要常常问自己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这种那么样清楚的、强烈的感受的话,你干嘛去?你去了跟你没去,基本上是一样的。也因此希望请大家去旅行,就千万不要去没有一点点陌生感的地方,你没有陌生感,一切都那么样的安稳,所有的人全部帮你安排的好好的,你就是上车下车,你就没有陌生感。
刚刚讲说我所坚持的态度跟立场,相当程度上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努力让自己保有这种陌生的心情。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读,我们读什么样的书?我一直都想阅读为什么那么重要,一直到今天为止,像你刚刚讲说,很多人现在看电影开弹幕对不对?看电影跟阅读最大的不同,因为看电影是画面所有东西都帮你准备好了,你可以一边散着这样看,为什么你还能够看弹幕,因为电影的讯息是那么样的固定,所以你还可以分神看一下弹幕。
你去读书,通常就不是这样,你一边看书一边有还有人在旁边跟你讲话。你能读书吗?我是绝对没办法的。为什么我觉得没办法,因为读书你需要专注,因为读书它就不是那么强而有力,文字不是那么强而有力的媒介,你如果自己不参与去想象去理解,你读不下去,但是也因为这样读书就比看电影好,对我来说在这一点上,因为文字对我们来说比较陌生,我们就会比较警觉去面对文字。
或许也是因为这样,现在到现在很多人一打开书就想睡觉,为什么?你看电影不会想睡觉,因为看电影比较轻松。这也是长远我们留下来的习惯跟跟经验,看书我们必须专注,我们必须正襟危坐,我们就觉得累,于是我们就睡着了。可是这是一个难得的人类文明中保留下来的一种刺激。
既然读书是这么回事,那就拜托不要读你很熟悉很容易读的书,你就浪费了。读书花下的时间,你就错失掉读书应该可以给你的刺激。所以刚刚讲说为什么应该要读古远一点的书,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书,以及平常你不会觉得一读就读得懂的书,因为这都是把你放到了这样的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去,所以突然之间你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你原来不觉得能够接受到的讯息被你接受到了,所以才引发出文道刚刚说的我的那样的一个态度跟提醒。
你干嘛在古人所写的书里面,要把它解读成为隔壁老王讲的话,我知道这听起来不好听,但我常常喜欢讲,就是说从我们叫“古书今读”或者是“经典现代解读”。如果说他的用意就是要把孔子的话、孟子的话解读到,听起来像是隔壁老王会说的话,你就去听隔壁老王说话就好了,你干嘛还要去读孔子和孟子?孔子孟子有价值,就是因为他在讲隔壁老王绝对不会说出来的话,不见得因为他们比隔壁老王聪明十倍百倍,这是另外一回事,隔壁老王跟我们活在同样一个环境里,没有这种陌生的刺激。
孔子、孟子,他们不了解我们,没有跟我们同样环境,因此他们遇到的问题,他们思考的方式对我们来说如此新鲜,我们不要错过这种新鲜感。这是我常常强调的,就是你反而只有到了古书里,才能够找到新鲜感。因为现代新的书,你以为叫做新的书,都是我们同代人所写的书,连我自己作为一个同代人,我都写不出新鲜的内容给我的读者看,但是如果我绕路去到了孔子那里去,到了孟子那里,我就可以找到很多新鲜的东西,这是回答你的问题,我为什么那么在意强调陌生感,其实是来自这里。
阅读与人的多样性:
现实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太有限了
梁文道:我觉得你刚才讲那个问题就牵涉到一个我们今天很多人对读书的态度的问题,你说我们为什么要把孔子读成隔壁老王?
我觉得今天相反的,我常常遇到情况是他们会反过来问,为什么我不该把孟子读成隔壁老王?市面上面常见到的那种书,就是说怎么样在跟朱子学工商管理等等。很多这类书,他们都是一种古书今读,都是一种试图要在古代的人写过的东西里面,找到一些能够回答今天的人最关切的问题的事情,更简单的讲或者更粗暴的讲法,就是他们希望很实用的去读这些书。否则你跟他说我们读书恰恰是要读出陌生感,就是要读出为什么古人关心的问题,比如说柏拉图关心的问题,绝对不是我们今天的人会关心的问题。既然他关心的问题跟我关系的问题都不一样,我干嘛要去读它?
当然是因为我要找出一些跟我今天有相关的东西,假如说柏拉图写的东西,你现在告诉我说,我发现他问的完全不同的问题,他的回答完全受限于他当年的思想资源跟文化脉络,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干嘛要读它?
然后你刚才的答案很有趣,你刚才答案是说,因为正是透过这样的操作之后,这样的一个头脑的转换之后,我才能够保持一种透过这种陌生感,我能够刺激自己,让自己变得更聪明。
这点让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我以前我们念哲学的时候,我们念一些古代的哲学书籍,最喜欢强调的就是这本书的problematic是什么?它的问题构架是什么?但是我后来发现问题构架这件事情本身,可能也不是古人会有的想法。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在读哲学的时候,我们太习惯,比如说读康德,很明显,康德是一个比较现代的哲学家,他写每一本书,他都有一个问题要解决,他有一个问题意识,他有一个问题构架,他依照这样的意识出发,去逐步的建构他的论证跟体系。
可是我能不能要求,比如说对于希腊的哲学也做同样的要求,比如说我读柏拉图的对话录,我甚至读先于苏格拉底的早辈的哲学家,比如说赫拉克利特,那些都是一些残篇断简,或者就是一些对话,我能不能去问他在关心什么问题,或者他的问题构架是什么呢?因为问这种想法本身就有一个预设,预设是什么?任何一部书籍,或者我们今天读到的文本,它都是一个完整的产物,它都是背后有一整套架构在里面,架构是依照他要处理的主题跟问题依序展开的。
赫拉克利特(前540-前480)
但是我们都知道以前的书并不是这样子构成的,《论语》甚至也不是。当然这就变成一个很大的争论,因为今天我们重新读这些古籍的时候,马上问题就来了。
比如说有一些学者,整部《论语》明明是个语录,他要把它读成一个很完整的体系。其实它不是一个随便编选的语录,它之所以编成这个样子,是这样的次序,是有这么多篇,这些篇如此结构,每一篇里面的话是如此的先后顺序排列,是有它的道理的,而这个道理其实是有一个构架在后面,而构架则是依照孔子或者他的门人们,他们的一个更最重要的问题来开展的。
但是也有一些人会反过来说,你这么就读错了,你等于拿了一个很现代的概念来读古书。因为在孔子那个年代或者在《论语》编成的年代,其实你要关注的是书到底是什么,什么叫做构成一本书。